桂林抗战文化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 者:邓群
出 处:中国共产党与桂林抗战文化
465抗日战争期间,随着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抗日文化中心的沦陷,位于西南地区的重要军事重镇和交通枢纽的桂林,逐渐成为全国各界文化人士聚集的地方。由于桂系同国民党中央势力有矛盾,出于保护地方势力的需要,为桂林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桂林在短期内吸引了大批的进步文化人士和爱国热血青年,各种文化团体也纷纷迁来桂林或在桂林创办文化事业,使桂林形成了蓬勃发展的抗日文化运动高潮这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创造了桂林文化城的奇迹,即在广阔的国统区内营造了一块‘特区’”。桂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著名的抗战文化中心,被誉为抗战“文化城”而影响全国,闻名世界。
桂林抗战文化在全民族抗战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士在桂林以“文人下乡,文章入伍”为口号通过各种文化艺术形式,宣传和发动广大民众,掀起抗战文化运动的热潮,在国统区树起民族抗战文化的旗帜,极具典型性,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桂林抗战文化不仅是党在文化思想战线斗争中开辟出的特区和创造的典型,而且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近现代民族解放斗争的宝贵文化遗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桂林抗战文化以民族大义为重,高举“团结、进步、民主”的旗帜,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极大地丰富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涵,弘扬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主旋律,团结了广大文化人士,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战文化运动的开展,培养了大批抗日文化新生力量,改变了西南地区文化落后的面貌;成为教育和团结人民大众,启发群众觉悟,积蓄革命力量,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促进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经验:同时,桂林抗战文化极为有力地推动了全面抗战、全民族抗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加强对桂林抗战文化历史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第一节 桂林抗战文化的地位
桂林抗战文化是中国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史,实际上是革命、进步文化和反动、倒退文化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通过领导桂林抗战文化,极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表现了深厚的爱国主义文化内涵;同时,它树起了团结抗战的旗帜,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文化专制和文化“围剿”。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取得的辉煌业绩;也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它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近现代民族解放斗争的宝贵文化遗产。
一、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
抗战时期的桂林,政治环境优于重庆,交通条件长于昆明,经济环境好于延安。这些有利的条件,使桂林能逸出重庆那种激烈的政治变动的中心,留出相对比较民主的政治空间,吸引上海、武汉、广州、香港等沦陷区来的大批文化人,出版大量的抗战文化书籍,组织多种形式的抗战文化宣传活动,使桂林成为抗战文化思想重要的交流地和集散地,许多外地编撰的书籍送桂林出版,如《国文月刊》由昆明的西南联大编辑,《新音乐》由李凌等在重庆编辑,《文艺战线》由周扬在延安编辑,《抗敌》由新四军抗敌社在华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编辑。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作家如刘白羽、周立波、中共中央东南局文委委员冯雪峰等也到过桂林。当时,“桂林是全国二大文化城之一,它拥有庞大的出版机构,它集中了全国文化人的三分之一,抗战时期的“精神粮食图书,有80%是由它(桂林)出产供给的,所以说桂林是文化城,不如说它是出版城更来得适当”。据统计,抗战时期国统区桂林虽仅有30万人口(抗战前为7万人),但在桂林抗战文化城战斗过的知名作家、艺术家和其他学者有1000多名;先后在桂林创刊和复刊的报纸杂志将近200种;在桂林开设的书店、书局、出版社有200余家,出版的文艺书籍有上千种;文化演出团体60余个,10多个剧种同时上演;群众性的歌咏会,诗歌朗诵会、街头诗画展盛况空前。桂林抗战文化的形成,既有国际的背景,又有国内的因素。桂林抗战文化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抗日文化运动、抗日文艺运动的开展。中国共产党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动员、组织与教育群众动员、组织各阶级各阶层群众投入全面抗战,形成全民族抗战洪流,既赢得了广大民主进步人士的赞誉,又提高了全民族的抗战文化意识,将全民抗战同争取人民民主相结合,不仅使桂林成为国统区重要的抗战文化中心,而且使人民大众抗日爱国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文化相融合,得到举国上下的赞同和认可,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成为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一面光辉旗帜。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战地记者曹聚仁在《报坛奇才萨空了》一文中提到:“我主编赣州《正气日报》时,那时后方文化中心在桂林。”《救亡日报》记者徐迟在《桂林分会是文协的心脏》一文中指出:“桂林分会应是(全国文协)心脏的地位……目前文协重要据点大致可有渝蓉黔滇桂港沪八个所在地,以桂林地点最适中进行工作这个联络员的责任,应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自动的负起。”“以桂林地点最适中”从客观上要求桂林分会文化人要“自动的负起”文化中心的任务,这是当年徐迟颇有独到之处的见解。《救亡日报》在《充满着朝气的桂林出版界》一文中指出:“自从广州失陷,武汉退出,长沙大火……许多出版物南迁了,许多文化人都集中桂林了……中国农村半月刊迁桂复刊后打破了桂林出版界沉闷的空气,接着救亡日报的十日文萃、国民公论、文摘、扫荡报、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在桂林相继复刊和发行桂林版以后,形成桂林出版界的空前的活跃…桂林的书店如雨后春笋样蓬勃,生活书店、新知书店、上海杂志公司、时代、黎明、中华、商务、前导、生路、北影…等十多家,代售着桂林的出版物和上海、重庆、香港各地的出版物,解放、群众、文化阵地、民族公论、读书月报、全民抗战、战时日本、妇女知识、世界知识、抗战文艺,其他的政治、军事、哲学、各种书籍非常之多……目前的桂林已经成为西南文化中心……报纸方面,香港的大公、星岛、大光、循环、工商、申报、星报……中华时报、南华早报(英文报)各大报,小报如天文台、探海灯等。”此文如实地报道了当时桂林抗战文化繁荣发达的盛况。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属政治部厅中共秘密支部支部委员的刘季平在《回忆我在桂林两年多的工作》一文中指出:“1938年秋,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进步文化人相继从上海、广州、武汉各地来到桂林,尤其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建立后,许多党员、进步人士,纷纷云集桂林,以桂林‘八办’为中心,展开了大量的党的政治活动。广西的政治局面,从这时开始越来越好,桂林逐渐成为我国西南后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建立,是我党在国统区工作上的重大决策,而贯彻党的方针,造成这样一个好的局面,周恩来同志是起着关键性,决定性作用的。”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
二、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深深懂得桂林在抗战中的重要战略意义,把它作为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在桂林部署了重要的文化力量,把从广州、武汉撤退的党的文化力量,一部分左翼文化工作者,由桂林“八办”统一安排到桂林的一些文化团体、众组织和广西当局的一些党政机关。在武汉沦陷前夕,周恩来派汉“八办”的副官刘恕和民主人士熊子民前往桂林,筹建桂林“八办”事宜。1938年10月25日,周恩来亲自做白崇禧的统战工作,并就桂林建立“八办”机构达成口头协议。11月25日至28日周恩来与白崇禧同时出席南岳军事会议,会后,周恩来与白崇禧就在桂林建立“八办”一事进一步达成协议。不久,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在桂林市桂北路宣告成立,处长李克农。
中国共产党广西地方组织先后在桂林建立20多个本地党支部,分别设在学校、工厂、三青团、学生军等部门。中国共产党外地党组织也在桂林建立20多个支部,分别设在各种文化机构、文艺团体中。本地与外地党的组织系统单向联系,不发生横的关系,在南方局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活动,通过集会、演讲、游行、座谈、办工人夜校开办职工服务社、发行报刊等方式,多渠道地动员群众,使统一战线工作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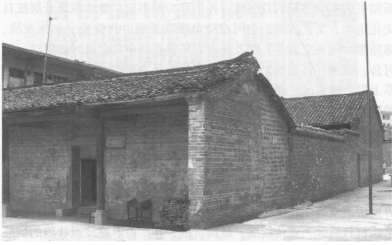
周恩来在桂林传达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龙王庙旧址
在桂林“八办”存在期间,周恩来于1938年12月,1939年2月、4月,三次到桂林,积极开展对桂系的统战工作,周恩来还公开接触文化界人士,建立广泛联系,利用一切机会扩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此期间,叶剑英、徐特立等领导同志也先后到桂林指导救亡运动和开展统战工作。叶剑英在桂林多次演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稳定了军心、民心,抵得上千军万马。”
桂林“八办”撤离后,1941年4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李亚群、刘隆华、孙士祥、徐鸣、胡家瑞(即何启君)等途径柳州到桂林,组建中共桂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强调桂林抗战文化阵地不能丢,“广西国统区与其他地区有差别,要充分利用这个差别,出版一些好书刊,不仅能在广西起作用,并要向其他国统区发行。”6月,中共桂林统战委员会成立,由李亚群任书记,其社会职业是新知书店实学书局的总編辑,孙士祥为副书记。继续领导开展抗日文化运动、文艺活动,会同在桂单线联系的中共党员(如张友渔、陈翰笙、司马文森等)以及与南方局联系的中共党员(如田汉、周可传、侯甸、吕复等)协助桂林统战委员会工作,一面继续搞好桂系上层与桂系民主派的统战工作;另一面组织理论、文艺、教育界的党员,团结教育党外知识分子,“做交朋友工作”,开展抗日民主活动、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活动。
三、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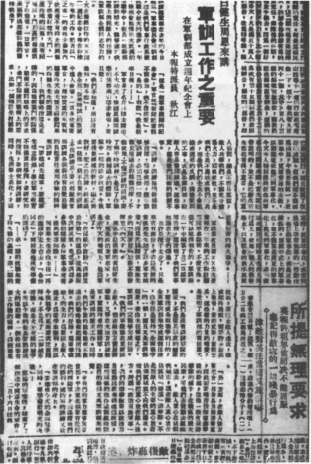
1939年2月16日周思来与叶挺应邀出席“军委会军训部成立周年纪念大会”作《军训工作之重要》报告
抗日战争是近现代史上中国人民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得到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援,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桂林抗战文化肩负历史使命,擂响抗日战鼓,宣传抗战、鼓舞抗战,在广西形成波澜壮阔的抗战文化运动,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发展,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殊的历史时期和桂林独特的地理位置,为世界反法西斯多元文化的交流构建了平台,大批的反法西斯国际友人共同为桂林的抗战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如日本著名的反战作家鹿地亘和池田幸子,日本世界语学者、作家绿川英子,苏联电影艺术家、摄影师卡尔曼,朝鲜的金若山、李达、李斗山、金奎光,越南的胡志明、范文同、武元甲,英国著名记者、作家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美国著名戏剧评论家爱金生,德国作家、记者王安娜,法国著名记者李蒙,英国的杰克等。一些国际组织和团体也从外地迁来桂林或在桂林成立,如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广西支会、桂林国际联谊会、英美设在桂林的新闻机构、中外文化协会桂林分会等中外友好文化团体等各文化团体和个人通过广泛的国际文化交流,赋予了桂林抗战文化的国际性,也使桂林抗战文化具有了开放的特性。

日本在华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负责人鹿地豆及夫人池田幸子在桂林
苏联记者卡尔曼在接受桂林各报联合采访时说:“我知道,各位的欢迎,并不是欢迎我卡尔曼个人,而是欢迎反侵略的全苏联人民,欢迎全世界反侵略的人民。我谨代表全苏联的民众,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向中国争取民族解放的斗士们致以最诚挚的敬礼!”“告诉各位,现在每一个苏联人民,都在睁着他们两只眼睛,热切地来看中国的英勇奋斗……看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战斗员之如何在艰苦中反抗;他们一直要看到日本法西斯被中国消灭,中国获得最后胜利那天的狂欢!”德国女作家王安娜说:“我有许多欧洲朋友,也有许多中国朋友,希望大家共同为和平而努力,打倒破坏和平的法西斯者。”越南的范文同在谈到中越抗战文化的一致性时指出:“我们越南革命党、越南文化界,始终坚决主张联合中国,打倒共同敌人。”桂林抗战文化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配合,在新闻、文学、戏剧等方面形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化。在桂林抗战文化城居住的文化人不仅写出了大量反映日本法西斯侵略暴行的文学作品,创作了贴近抗战民众生活的话剧、歌剧和舞剧,而且还翻译、介绍了大量外国作品。如郭定一译的《夏伯阳》(富曼诺夫),邵荃麟译的《游击队员范思加》(弗兰欧门),茅盾译的《复仇的火焰》(巴夫连柯),曹靖华译的《虹》(劳伦斯),林举岱译的《在乌克兰草舍中》(瓦希列夫斯卡),朱雯译的《地下火》(H·列普曼)。桂林出版的文艺期刊如《文艺杂志》、《文艺生活》、《文学创作》、《创作月刊》、《当代文艺》、《青年文艺》、《青年生活》、《自由中国》、《人世间》、《新文学》、《新音乐》、《戏剧春秋》、《文化杂志》、《文学集林》、《中学生》、《野草》、《诗创作》、《半月文艺》、《半月文萃》、《十日文萃》等40余种杂志都辟有翻译专栏,翻译和介绍了不少苏联及世界各国作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创作的反映现实斗争的小说,也介绍了各国文学近况和不少的评论或书讯,增进了文化的交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司马文森和艾芜等人的小说也被翻译成外文出版。这些文化交流,凝聚了更加广泛的抗战文化力量,使桂林抗战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创造了抗战文化运动的奇迹。

朝朝鲜义勇队、缅甸华侨义勇工程队上街游行
第二节 桂林抗战文化的作用
亲身经历过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千家驹说:“若从某种意义上说,桂林抗战文化城在抗战中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过重庆。”杨益群先生说:桂林抗战文学是“是抗战文学凝聚点”,因此,桂林抗战文化是中华民族抗日文化运动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于鼓舞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推进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为:

国民政府西南行营办公厅主任李济深发表抗日演讲
一、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桂林抗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努力追求先进文化的心血,极大地丰富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涵,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通过严密的组织系统,为桂林抗战文化提供了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著作等文化思想理论和人才资源,在桂林抗战文化城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一系列的抗战文化活动,调动了各阶级各阶层的抗战文化力量团结了广大的爱国民主进步人士,提升了桂林抗战文化的伟大作用。中国共产党对桂林抗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是桂林抗战文化的坚强领导者,是中国人民神圣抗战精神的支柱。桂林抗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以及《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化座谈会上讲话》等毛泽东著作在桂林广泛传播,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及文化、文艺思想在桂林得到了实践,“文人下乡,文章入伍”的抗战文化口号得到了实施。如文化供应社出版了一套《新道理》的通俗刊物,组织编撰了包括国民必读、妇女读物、士兵读物等200册系列文库。
桂林抗战文化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征,其中在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中取得成就的大多是共产党员、进步文化人士,如巴金不仅在桂林完成《还魂草》、《某夫妇》等小说,而且同赖贻恩进行了“提高生活标准”与“提高道德标准”的论战,这些为当代文化价值的构建提供了一定的借鉴。茅盾在桂林创作了《霜叶红于二月花》,是他刻画“规模宏大的历史画卷”、反映“中国民主革命的艰苦历程”的一部重要作品,它“为我国文学宝库创造了珍贵的财富,提高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水平,在文学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夏衍在桂林创作了《心防》、《法西斯细菌》等优秀剧本,田汉在桂林创作了话剧《秋声赋》、《黄金时代》,戏曲《梁红玉》等。进步文化人的创作,极大地丰富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涵。
二、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的主旋律
随着战争时间的推移,桂林逐渐承担起抗日文化运动中心的使命,我党正确地分析形势,看到了在桂林建立抗日宣传据点的战略意义。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桂林部署了重要的文化力量,这些文化力量以笔为武器,宣传抗日。在“立人下乡,立章入伍”的号召下,文化人士纷纷走上街头,走向部队和农村,进行抗战演讲。抗日救亡的歌声,响彻桂林以至广西城乡各个角落,一切都在“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歌声中进行;一切都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开展活动。夏衍率领《救亡日报》社全体同志自广州撤退迁到桂林,立即成为桂林挽救民族危亡,高擎爱国主义大旗的战斗群体,成为推动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火车头。当时,宣传抗日救亡,举起爱国主义大旗的除了《救亡日报》等报刊外,最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是群众的歌咏活动。1937年冬,桂林第一个歌咏团由广西音乐会和国防艺术社联合组织起来,将所有的音乐专业人联合起来开展群众性音乐运动,一时间形成很大的规模,报名参加歌咏团的单位有32个,团员达5700多人。此外,大中小学校、机关团体都组织歌咏团,职业的文艺团体都有专门的合唱团。当时,广为传唱的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军民合作歌》、《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游击队歌》、《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黄水谣》、《长城谣》、《松花江上》、《全国总动员》、《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桂林举行过数千人的火炬大游行,唱着抗战歌曲行进,使得街道两旁的人民群众跟着火光跟随着歌声跳动。当时,在体育场举行了“万人大合唱歌咏大会,雄壮嘹亮、怒吼如涛的歌声,从地层深处传递到所有文化人和人民大众豪迈的心坎之中,令人终生难忘。这样大型的抗战群众歌咏活动,经常举行。那时候,几乎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抗战的歌声;哪个地方的抗战歌声最嘹亮,就表明那个地方民众动员最广泛。冼星海说过:“这种雄亮的救亡歌声为中国几千年来所没有,而群众能受它的激荡更加坚决地抵抗和团结,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一种音乐史迹。”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群众歌咏活动,谱写了中国音乐史上最灿烂的乐章。
桂林抗战戏剧运动,主要表现在以爱国主义为主旋律的各类剧种中。话剧是最受群众欢迎的一种最活跃的剧种,许多话剧担负了动员和教育群众的任务,如田汉的《秋声赋》、《再会吧香港》,曹禺的《蜕变》、《雷雨》,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夏衍的《心防》、《一年间》,洪深的《包得行》,丁西林的《妙蜂山》和外国反法西斯话剧《复活》。其他的歌剧、舞剧、活报剧《怒吼吧桂林》、《虎爷》、《军民进行曲》、《放下你的鞭子》等都是唤起人心、激励不愿做奴隶的人民起来奋勇杀敌的、弘扬民族精神的爱国主义戏剧。欧阳予倩、田汉等戏剧名家对旧剧如桂剧进行改编的剧本《梁红玉》、《木兰从军》、《广西的娘子军》等,都渗进了剧作家和导演们的爱国主义心血,鼓动工、农、兵奔赴抗日的战场,保卫可爱的中国。我们可以从戏剧演出的相关统计数字,了解桂林抗战戏剧运动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的盛况:从1938年11月至1944年5月这6年多时间,桂林演出话剧600场(剧本400个)。演出桂剧、评剧湘剧、粤剧等地方戏500场(剧本280个),歌剧、舞剧30场(剧本15个),举办音乐、文艺晚会近300场,演唱演奏歌曲410首演出舞蹈节目40多台。此外,职业的和非职业文艺表演团队经常深入工厂、农村、学校、部队、街道的演出,场次不计其数。在举办群众歌咏活动、抗战音乐会的同时,桂林还以其他形式,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活动年12月1日,桂林市数万群众举行保卫大西南运动大会,通电慰劳前方将士,表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集中一切力量,军民合作,予敌寇以迎头痛击。”1940年,桂林市各团体举行了三大义务劳动,妇女界制作了3.38万朵纸花,出动54个义卖队。1944年2月到5月,桂林隆重举行西南戏剧展览,将桂林抗战文化推上发展高峰,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具有强大的号召力。西南剧展后组建了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和文化抗宣队,举行了扩大抗战动员周、国旗献金大游行。为保卫桂林抗战文化城、为全民族抗战到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培养了有战斗力的文化新生力量
桂林抗战文化是中华民族为生存而孕育的一种革命文化现象它的全部活动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与战斗精神,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学、文化、卫生、体育、戏剧、诗歌、音乐、美术、文艺评论等一系列领域,为培养新生文化力量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1940年9月,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学员学习的情景
1939年建立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培训了1400余名干部,师生中绝大多数人成为抗战文化工作者和抗日民主战士;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开展抗日文化宣传,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全面抗战、全民族抗战、持久抗战,被誉为“南方抗大”,是中国共产党传播抗战文化的重要阵地。1940年夏秋,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派干部分别到柳庆区、浔梧玉区、邕龙区开办干部或村街长训练班共五期,训练人员达2000余人,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对干部、村街长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把党的宣传阵地扩大到全省。桂系培养人才的桂林师范(前身两江师范),受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广西省工委要求当地党组织要“把桂师办成我党教育青年,培养骨干的场所”。桂师中的许多学生都是桂林开展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和文化运动的骨干力量。据桂林师范校史记载,该校9年间培养了900多名学生,很多人入了党,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有400多人参加游击队或党的地下工作,有40多人为革命献出年轻的生命。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在向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汇报的《广西党报告》中,称赞桂师学生“都是受了进步、民主思想的熏陶”,这些学生“六七年来都是我们领导与掌握的,他们一批批毕业后深入农村,进行民主文化教育工作”这些力量“对于今后的斗争将起很大作用”。桂林文艺界通过举办文艺讲习班,创办青年文学刊物,积极培养战文化骨干,使陈迩冬(广西师专学生)、秦似、秦牧、严杰人(有“中国神童”诗人之美誉)等抗战文化人士脱颖而出。

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行政办公室旧址
桂林抗战文化城发达的出版业和众多的文化人,将心血凝成的精神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往全国各地,不少作品翻译成外文在国内外出版。这些书籍有政治文化思想读物,有小说、诗歌、散文、杂文等文艺作品,展示了“人类进步文化的一个血的浸润和血的灌注过程。”学术团体和社会科学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桂林的社会科学团体有广西建设研究会、广西教育研究所、生活教育社等,大型的刊物如《克敌》、《全面抗战》、《文化杂志》、《中学生》等。《新华日报》桂林分馆、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文化供应社等进步文化单位积极出版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为桂林抗战文化提供了必要的思想理论武器。桂林抗战文化在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史学、哲学等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哲学方面,如杨东莼发表的《理论与实际》,已经论证了实践是理论试金石的命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是值得后来的学者学习的经典文章。在文学方面有,巴金的散文《在广州》、《桂林的受难》、《桂林的微雨》、《先死者》、《轰炸后》等,夏衍的通讯《在废圩上生长的》,艾芜的散文《桂林遭炸记》,戈衍棣的散文《桂林的毁灭》,郭沫若的诗歌《罪的金字塔》,艾青的《死难者的画像》,邹绿芷的《丑恶的硒像》,黄药眠的长诗《桂林底撤退》,吴奚如的小说《肖连长》、《吹号手》,骆宾基的小说《仇恨》,谷斯范的小说《新水浒》,王鲁彦的小说《胡蒲妙计收伪军》、《杨连副》,于逢、易巩的小说《伙伴们》,孙陵的散文《突围记》,朱雯的故事集《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等;诗歌有艾青的《吹号者》、《他死在二次》,田间的《给战斗者》、严杰人的《今之普罗米修士》等,这些作品弘扬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气节,爱国主义精神和宁死不屈的战斗意志,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决心。
四、中国抗战文化是对外交流的重要纽带
抗战以前,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是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上海沦陷,作为我国南大门的广州,成了我国与港澳及海外联系的交通枢纽,同时也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但随着广州的沦陷,桂林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作用日益凸现。在一段时期,桂林成为国际友人进行反法西斯文化活动的聚集地,许多爱好和平的国际组织和友人来到桂林开展抗日宣传。如朝鲜李斗山的《1940年进行曲》;鹿地亘的剧本《三兄弟》;胡志明的《安南歌谣与中国抗战》等,都表达了和平的愿望和对中国抗战事业的支持。苏联的摄影记者卡尔曼到桂林以后,把新安旅行团及广西学生军第一团的训练拍成影片,“带到欧洲,带给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遵照党的指示,1939年4月下旬,在谢和赓的巧妙安排下,中国救亡团得到李宗仁、白崇禧的同意,在金山、王莹的率领下,从桂林出发,经香港、西贡、新加坡、马来西亚诸岛演出抗战戏剧《台儿庄大捷》、《塞上风云》、《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该剧团用近两年时间,行程两万里,筹集到5000万美元的经费,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战,在东南亚以及国际上都产生巨大的影响。1940年10月,胡愈之到南洋进行抗战文化活动,在南洋各地创办抗战杂志,发行桂林出版的《救亡日报》、《国民公论》,《战时文摘》、《十日文萃》等。由于国内外文化交流活动频繁,桂林抗战文化城不仅成为国统区西南大后方的抗战文化中心,而且也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化战线,成为联系世界反法西斯文化力量的重要纽带。
总之,桂林抗战文化在推动各族人民参加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抗日文化运动、抗日文艺运动、民主革命运动中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它号召国共两党、各民主党派、各阶级各阶层爱国民主进步人士,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共同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努力奋斗。桂林抗战文化吹响了全民族抗战和全面抗战的时代号角,谱写了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

抗战时期在桂林的著名作家巴金(左)

著名音乐家张曙墓(在七星岩豆芽岩斜对面)
上一篇:抗战文化在桂林
下一篇:桂林文化活动出现空前的活跃

联系电话: 0773-3609555
邮政编码: 541100
桂林·抗战文化 桂ICP备06000626号 技术支持:万卷文旅&人人通